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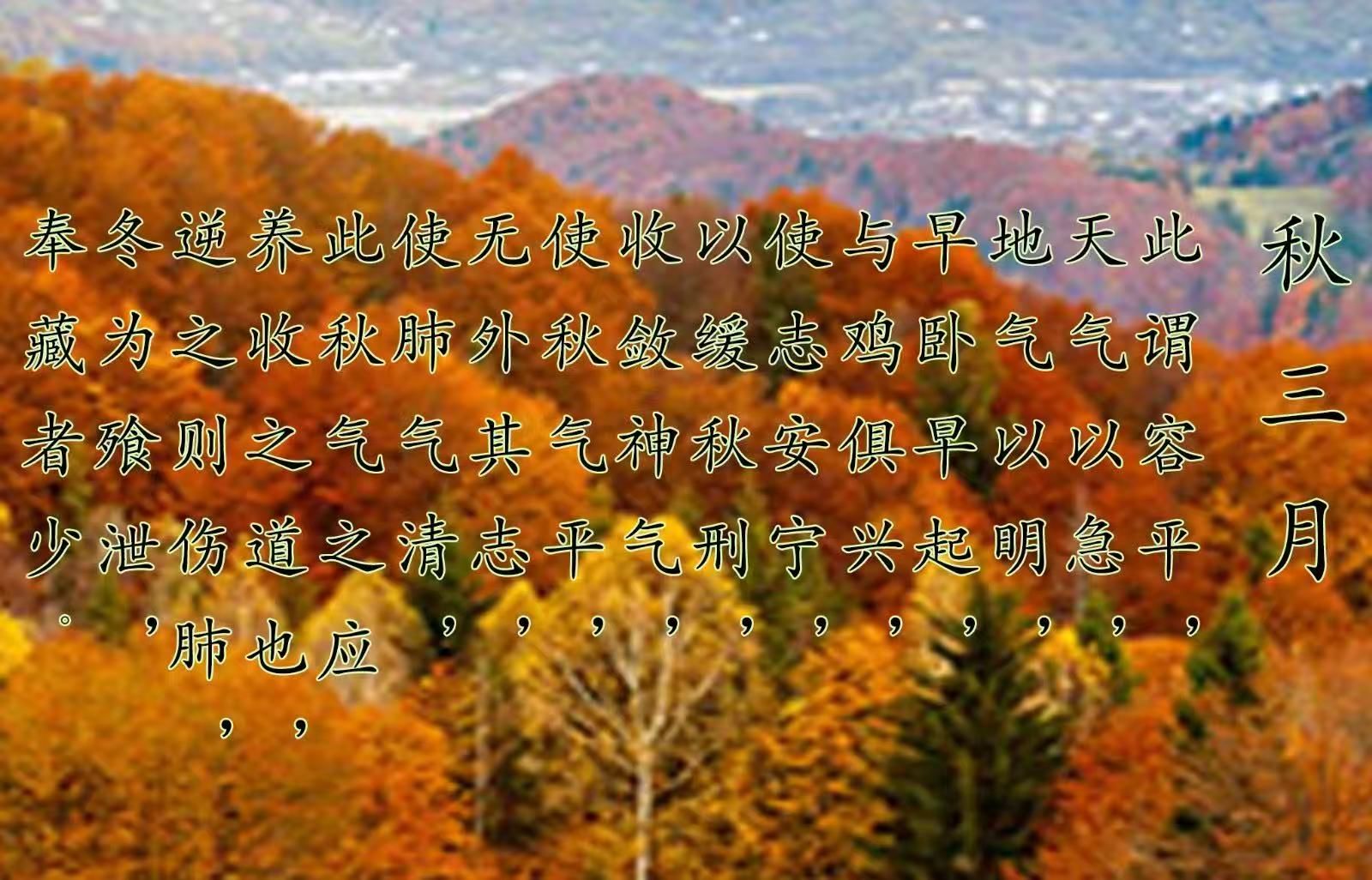

集体广播操
作者:宋合营
广播体操归去来
沉寂多年以后,这项在国内普及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群众性体育项目又突然复活了。只是,当年那个“万人齐做操”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8月的北京,凉风渐起,久违的旋律从大喇叭里扩散开来,飘送到一个又一个耳膜里。人们成群结队地走出办公室,在市总工会大楼前后的空地上,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太庙广场上,在西单商场的柜台前,到处伸胳膊踢腿儿,做起熟悉又陌生的集体操。
年过七旬的陆奂奂和刘西玉待在各自家中,一边指挥小时工打扫屋子,一边监督小孙女做暑期作业。收音机没有打开,屋里也听不到外边的喧闹,她们没有跟大家一起做操。然而,这两位老人却与广播体操有着异于常人的联系:陆奂奂曾参加过多套广播体操的意见征求和后期推广,刘西玉则直接参与创编了第六和第八套广播体操。
广播操诞生
1951年,彼时的陆奂奂16岁,就读于杭州一所高级中学,瘦弱,贫血,每顿饭能吃上两片梅干菜烧肉,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13岁的刘西玉,在成都一家普通初中念书,从学校到家,需要走很长一段路,路上经常可以看到牵着小孩的大人,沿街乞讨。
这一年的11月24日,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
当时的国家,也处于百废待兴的关口上,民族体质整体偏弱,根据史料记载,建国之初,我国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当时的老百姓既没有体育锻炼的意识,国家也拿不出钱来建设体育场馆。偌大的北京城,只有一座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正规体育场——先农坛体育场,除此之外,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都没有。
筹备中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直属机构,与后来的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决定,配合国家优先恢复经济的整体规划,不搞大型运动会,着重抓普及。
筹委会里有个叫杨烈的女干部,曾于1950年8月赴前苏联考察学习,回国之后,她手写了一份报告,递交到体总筹委会,建议创编一套“适合徒手锻炼”的全民健身操。后来,这份报告成了我国开展广播体操运动的缘起。
由北京日报社编写的《历史的背影》一书,记录了更多细节:筹委会里另一名叫做刘以珍的女干部,承担起了编操任务。她曾师从于日本教师,学过一种被称作“辣椒操”的广播体操(日语发音类似“辣椒”),借鉴这套操的基本框架,再加上自己的创新,刘以珍很快编出了新中国的第一套全民健身操。在传播途径上,也同样采取了广播样式。
第一套广播体操颁布当天,人民政府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推广活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9家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大家都来做广播体操》。又过了一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广播体操节目,每天上午10点,激昂的旋律都会准时响起。人们开始合着节拍,整齐划一地做同样一种体育运动,场面蔚为壮观。很快,北京、天津、上海等40多座地方人民广播电台都陆续在同一时段转播该节目,广播体操的声势越来越大。
然而,即便如此,广播体操所能覆盖的人群,依然是有限的。陆奂奂和刘西玉分别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她们当年都没有做过第一套广播体操,而且也没有看见父母或其他家人做过。“那时候大人整天忙着上工,从来没有体育锻炼的意识,我们在学校上体育课,也就是跑跑步、打打篮球,业余生活单调得很。”刘西玉说。
这很可能与广播安装不够普及有关。史料记载,当时国内尚有一些地区收听不便,或者收听设备不完善,为解决这一问题,人民广播器材厂还加班加点,先后供应了3800张“广播体操”唱片。
集体主义情结
时间很快来到1954年的夏天,陆奂奂已经是中央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前身)的学生,刘西玉也已经顺利考入了成都体院的高中部。
这年7月,改良版的第二套广播体操公布了。在此之前的3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史无前例地以“总理指示”口吻发布通知,要求全国各机关“在每天上午和下午的工作时间中抽出十分钟做工间操”,“做操时,应动员所有工作人员参加。领导干部应负责组织领导,并带头参加,使之能够组织起来,坚持下去。”
刘西玉看到,大喇叭迅速挂上工厂和校园的树梢,老师们也集体做起广播体操来了。陆奂奂也开始跟着老师、同学深入工厂,了解一线纺织女工的生活,义务帮助她们编排适合她们岗位需求的工间操。
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卢元镇曾形容当时的广播体操热——“一到点儿放广播操,商店里的顾客和售货员一块儿做操;在火车上,正好停靠在哪个站上了,大家都下来在站台上做操;甚至就在列车上,大家都站起来做操。”
除了中间“三年自然灾害”对人们体力上的削减,以及“中苏断交”导致“劳卫制”改名以外,高涨的全民体育热情几乎没有间断,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期间,第三套广播体操和第四套广播体操陆续颁布,拍摄于1962年的喜剧影片《大李、小李和老李》,生动地记录下了众人齐做第三套广播体操的场景:车间工会主席大李,原本不爱锻炼,被选为体协主席后,他到新华书店去买广播操图解,不想那里已经卖完,只剩下残破的半张,女售货员当场就边示范边给大李讲解。回家后,大李又叫儿子教了自己一段少年广播操。第二天,他带着这套不伦不类的广播操给大家做示范,当场闹出了大笑话。
接下来,“文革”来了,原本简单轻松的广播体操,迅速被承载了阶级斗争功能的“语录操”代替。这种操与广播体操的套路相似,只是给每个小节都添加了毛主席语录内容,动作表现上也灌注了强烈的情绪,人们在做操的同时,高声朗读语录。
彼时,已经是北体大(当时的校名是“北京体育学院”)教师的陆奂奂,曾参与这套“语录操”的创编工作。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鹤发童颜的她丝毫没有忌讳什么,“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上级给我安排了这个活儿,我就编了。”“你说丝毫没有掺杂个人情感?那也不正确,我也想着‘排除万难,不怕牺牲’(语录操中的内容),只是我不把它当做谋取个人权力的工具,纯粹是用来鼓励自己要努力、要奋斗。”
挑战者
“文革”风潮到1971年时,已经逐渐减弱,“语录操”很快退出历史舞台,重新修订的第五套广播体操新鲜出炉。人们似乎又重新回到了集体做操的火热年代。
在这套操推广期间,北京厂桥小学的一名小学生,因为做广播体操姿态标准优美,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一则新闻简报意外记录了他的身影。正是因为这次露脸,让什刹海体校的老师发现了这个很有运动天赋的孩子,把他选拔进了体校,专门练习武术。这个孩子后来成了蜚声海内外的“功夫巨星”,他就是李连杰。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第五套广播体操仍带有“文革”色彩。在整套动作正式开始前,广播里先用一小段慷慨激昂的话开篇:“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在具体动作上,则明显加入了武术元素。陆奂奂照着图解给记者演示了其中部分小节,可以明显地看见握拳和冲拳的动作。
“当时国内掀起了一股武术热,做广播操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刘西玉说。当时,她也已经接受了北体大的系统教育,成为该校的一名老师。不久之后,第六套广播体操的编操任务,落到了她和几个同事的身上。
1981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步履初开,来自海峡对岸的“靡靡之音”最先酥麻了人们的耳朵。柔若无骨的邓丽君歌曲,透过收音机听筒悠悠飘来。刘西玉敏锐地意识到,单靠传统的广播体操编排样式,已经很难吸引新时代的年轻人。于是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编操时,刘西玉首次找来两名作曲家为这套广播操配乐,一个是著名作曲家刘炽,另一个是总政军乐团的傅晶。两人谱出的音乐一套沉稳舒缓,一套轻快俏皮,均不同程度地糅合了民乐和交响乐元素,今天翻出来再听,仍然不乏鲜明的趣味性。
但尽管如此,广播体操的“大一统”地位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式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崇尚个人躯体健美的健身操运动开始风靡,1985年,央视为一个名叫马华的女教练专门开了一档叫做“健美5分钟”的栏目,迅速火爆全国。1987年,美国电影《霹雳舞》被引进国内,再次引发霹雳舞热潮,年少轻狂的中国青年们扎堆聚在一起,比拼“擦玻璃”、走“太空步”、蹦“迪斯科”,High到满脸潮红。
老年人似乎也找到了更多的乐子。太极拳、秧歌、气功、空竹、柔力球,活动形式越来越丰富多彩。进入90年代和新世纪以后,瑜伽、跆拳道、国标舞也相继传入,不同年龄段和收入阶层的人们,总能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曾经辉煌得无以复加的广播体操,此刻被人们遗忘在看不见的角落,愈发显得机械、僵化。这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1987年前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停播广播体操,几乎在同一时间,各地方广播台的广播操节目也陆续在电波中消失了。包括陆奂奂和刘西玉在内的所有人,几乎都未能关注到这一微妙变化。《中国体育报》曾有记者就此致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受采访的多名工作人员无一能说清停播的来龙去脉。
唯一能给出一点解释的是央广总编室副主任李宪力,他回答说,“现在社会上什么磁带都有,广播操的磁带也可以买到,许多单位可以根据时间自己放曲做。我们曾对收听率进行过社会调查,很少有单位做了。广播电台也得注重市场,市场需要什么我们才播什么。电台没有太多的义务每天播放广播操。”
电台不给放,电视台可不可以呢?彼时的陆奂奂,已经调任到体育总局下设的体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她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她曾经多方联系电视台,试图说服他们安排播出广播体操的音乐或视频,结果,后来只有一家电视台勉强给安排了一档少儿广播操的节目。成人操,则一直无人问津。
“政治”操
是不是又该推出新的广播体操了?1990年,国家体委组织专家着手编创第七套广播操,陆奂奂是参编专家之一。专家组似乎强烈感受到了外部竞争的压力,他们尽可能地各抒己见,最终竟拿出了一易一难两个不同的版本一起推出,有做操需求的单位,可以根据自身需求灵活选用。
翻看较难版本的那套广播操,动作中明显加入的韵律操的内容,做起来已经十分繁复。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后来对这套操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他以其中的“跳跃运动”一节举例谈自己的做操感受,“手脚都倒换不过来,又是前又是后,又是左又是右,又是上又是下,智商低一点的,可能还做不了。”
1997年4月,第八套,也是最后一套广播体操出炉。参与创编的刘西玉回忆说,当时专家组成员在思路上有了明显的转变,力求使其重新回归到“科学、简易、基本、普及、通用”上来。
在这项转变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伍绍祖。他曾对广播体操和其他运动做了清晰的划分:“广播体操的性质就是官方操。这个操的作用就是号召大家都出去活动,到了操场,先做广播体操,活动开了,你愿意打拳就打拳,你要跳舞就去跳舞,做什么活动都可以。官方操是我们提倡的,没人做也得搞,因为这是个举旗帜的操。这个操是个‘政治’操,不是业务操。”“再者,这是一种交流操,比如说官方组织会操,大家统一比赛,需要规定动作,官方推出的操就是统一的。所以,既是官方提倡的,又能够交流,又能够会操,它的性质定义就出来了。”
不知是不是因为这段话的传播,后来广播体操原先的全民参与色彩日益淡化,人们越来越习惯看它出现在大型运动会的队列仪式,或者各种机关团体的广播操比赛上。
刘西玉的学生、第八套成人广播体操创编组组长程再宽,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意味深长地感慨,“很多参赛队都把动作练得非常标准,整体效果也齐刷刷的,一点看不出什么破绽。我们评委私下一了解,原来是有的企业为了取得好的名次,专门培养了广播操参赛队伍,甚至还有脱产专门练这个的。”
“我十分不赞同这种做法,”程再宽说,广播体操的主要功用还是为了引导大家锻炼身体,“过分将其形式化、功利化,反而不利于正常的职工体育活动开展。”
与此同时,一些不得不每天做广播体操的中小学生,在做操时故意改变或加入一些自选动作,在互联网上被笑称“操帝”,程再宽却觉得很正常,“只要是能起到锻炼身心的作用,不按规定套路来,也没什么要紧。”
昔日重来?
时隔13年之后,第八套广播体操被北京市总工会重新发掘出来,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体育广播又重新播放起做操的音乐,这是陆奂奂和刘西玉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你能先给我讲讲是怎么一回事吗?”约访过程中,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地问《中国周刊》记者。
媒体报道中的起因,说是来自于北京市人大代表邹晓美的“两会”提案。提案中说,一些职工长期在电脑前工作,没有像学校那样的课间操运动,导致一些人出现疲劳、肥胖、腰酸等亚健康状态。她认为,这一现象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对此,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李丽莉回复说,工间操已经被列入《健康北京人——全民健康促进十年行动规划》,主要以第八套广播体操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太极剑、韵律操等项目。
8月10日,承诺兑现,几家单位在太庙前启动了声势浩大的“首都职工示范推广工间操宣传周”活动,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带领3000名来自各行业的工间操教员齐做广播操,李宁、杨杨、杨凌、董炯、李素丽等社会名人到场担任形象大使。
这一举措的示范效应很快影响到其他地方,长春、济南、南京、常州等城市接连奏响广播体操旋律。
然而,这场带有强烈怀旧色彩的群体活动到底是一时兴起,还是就此走向了凤凰涅槃后的重生?陆奂奂和刘西玉都说,她们无法看清。
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推动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开展,其合理性也很快遭到了人们的质疑。根据媒体的报道,北京市总工会已经定下目标,“2011年全市职工参与健身活动比例要达到60%以上,国有企业参与工间或工前操活动要达到100%,机关事业单位要达到70%”,具体实现办法是,将工间操开展情况纳入对各单位“一把手”的考核内容。
香港《大公报》很快就此发表评论,全民健身活动不应上升至“一把手工程”高度,“那些早已千头万绪、应接不暇的‘一把手’们,就饶了他们吧,别让他们‘累着了’。”
几天后,北京市总工会出面澄清,说所谓的“‘一把手考核”指的是各单位工会干部中的“一把手”,而不是整个机关、企业的“一把手”。
但接下来又有问题,众多企业与国企和机关团体不同,工会如何对他们展开监督?截至目前,北京市总工会还没能给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现在,陆奂奂和刘西玉的主要锻炼方式是散步,或者是跟其他老头、老太太一起打打太极拳,跳跳老年舞。偶尔胳膊酸、脖子疼了,也会做几个体操动作舒活舒活筋骨。“如果硬要我去参加群体性的广播体操,可能我也会过去,但心里总归不是很情愿。毕竟,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陆奂奂理了理满头银发,微笑着说。
